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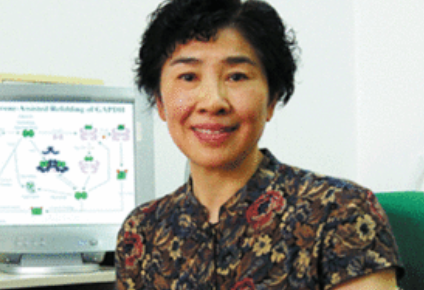
王志珍院士
王志珍,1942年生,江苏吴县(现苏州市)人。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分配在生物物理所工作。在胰岛素A、B链相互作用及重组,蛋白质折叠、折叠酶和分子伴侣,内质网氧化还原稳态与疾病等领域做研究工作。 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后改名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曾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基础科学奖(生物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二次;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三次;“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妇女”;“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中国十大女杰”等奖励。曾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访:王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所里正在做所史研究。研究所各位先生们的科研工作也就是研究所科研工作的主线。所以,今天想请您谈谈,您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以及您觉得值得记录的一些事情。
王:我195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5912班)。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我从初中开始成为上海中学校体操队队员。1958年,学校安排几位体操队队员去上海师范学院体育系体操专业脱产集训,希望培养出体操一级运动员。那时我读高三,还有大半年就要考大学了,我很不愿意中止学业去参加体操集训。我哥哥是共产党员,他对我说:“一定要服从党的分配,但是晚上一定要自学,我相信你可以靠自学考上大学。”那半年,我白天与体操班的学生一起训练,晚上坚持高三课程的自学。我终于通过上海市的考试获得了“体操一级运动员”称号,完成了学校交给我的任务。但也因为我是一级运动员,考大学填志愿时学校要求我报考体育学院,这与我一直以来想学理科、报考一类(理工科)大学相矛盾。当时班里为此还排了个节目在学校演出来“帮助”我。后来我的班主任白老师突然通知我:“你可以考一类大学了”,我开心得不得了。几十年后的老同学聚会上,我向白老师问起这件事。他就讲了一句话:“你是三好学生嘛”。我理解校领导是非常讲大局也非常爱护学生的。中国科大生物物理系是我的第一志愿,后面填了清华、北大的几个系。
访:那时报志愿都是学校决定的?
王:老师了解学生,学校也了解国家培养人才的计划和布局,所以老师会给一个指导性意见。记得老师推荐班里一个同学去考北大英语系。那个同学说,英语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不想去学。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老师的建议,考入了北大英语系,后来成为《参考消息》的主要业务负责人。还记得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考上大学以后,被通知不能入校,我们非常震惊,也为他难受。
访:请您谈谈进入生物物理所工作后的情况。
王:我的毕业论文是在三室做的,是一个浓缩噬菌体培养液的小实验,不能与我们现在学生做毕业设计的训练相比。从科大毕业,我想考研究生,但是系主任沈淑敏先生找我们四、五个同学说,“希望你们留在生物物理所工作,不要去考外面的研究生。”当时我们的思想就是听组织的话,服从分配。
1964年,我们这一批毕业生来所里报到后,很多人直接去山西洪洞参加“四清”运动。我则被分配到研究放射生物学的二室赵克俭老师组,后来又被调到了李公岫老师组。那时候研究工作的组织和机制与现在完全不同,效率也完全不能与现在相比。我记得我做的第一个实验是移液管的体积矫正。
第二年我才被批准参加了在运城的“四清”,一年后回京参加“文革”。回想起来,“四清”的一年对我们这些“三门”(家门,学校门,单位门)人员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还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当时贝时璋先生被安排在李公岫组参加“文革”,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大家一起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及各种通知、文件。这段时间我的极大收获就是天天与贝老在一个组里学习、活动,听他讲了很多个人经历。如贝老是中农家庭出身,是由亲戚朋友一起凑钱给予资助到德国留学的等等。我记得贝先生还讲过一件事,蒋介石请很多大科学家吃饭,他也应邀出席了,贝先生感到这是一辈子最大的耻辱。
“文革”期间我怀孕有较严重的反应,在一次早请示的时候晕倒了。室革委会的一个领导说:“王志珍,你早不晕晚不晕,就是在早请示时晕是什么意思?”,把我怀孕的生理反应上纲到政治态度,后来还散布说我是癔病,癔病是一种精神病。现在说起这些事,我没有任何责怪个人的意思,只是想说灾难性的“文革”把一些人的思维和心态扭曲了、畸变了。
访:“文革”期间,您还去首钢工作过一段时间?
王:当时陈伯达要求我们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和中学去接受工人、农民和中学生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去了首钢。
我们队有高麟征、呼俊改和我三个女同志,从中关村到首钢不是坐车去的,是行军拉练去的。首钢的生产环境非常严峻,我们每天在转炉前三班倒。听说钢铁学院毕业的女生都没有在转炉前工作的。当时首钢流行肝炎,我和陈景峰得了急性肝炎。特别令人惋惜的是,我们的组长黄家忠得了肝癌后去世。黄家忠是我们的好组长,他总是把最危险、最艰难的工作留给自己,吃苦在先。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都非常怀念他。这一年炼钢工人的劳动生活对我们是极大的考验,但使我了解了大工业和产业工人,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
前些年我因工作原因去过一次石景山,但是首钢已经搬走了。后来有机会到曹妃甸,我如愿去了首钢,已经是炼钢完全自动化的首钢了。
访:您去干校了吗?
王:我去了半年干校,在大兴农场。90年代有一次我到美国开会,在饭店里吃饭时,发现旁边桌上有个人老看我。随后他走过来问我是科学院的吗?一说才想起原来是当年大兴干校的同学,他那时在计算所。过了这么多年却在美国的一家餐馆里巧遇,真是挺有意思的。
访:从干校回来后,您做了哪些工作?
王: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李元庚书记、韩兆桂处长、徐秀璋书记。他们在我的科研生涯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当时二室的书记李元庚是一位转业军人。“文革”以后,所里的研究工作几乎完全中断。我每天都跑到李书记的办公室,请求让我工作:“李书记,我不愿意这么坐着,请你把我调到任何一个只要有事情可以做的地方”。李书记虽然很为难,但没有责难我,也没有批评我。一天,李书记跟我说,“组织上同意把你调到胰岛素组了。”我高兴极了,我终于可以做工作了!
在胰岛素组,我的工作是做胰岛素的生化研究。当时一起做实验的有从上海调来的雷克健,他是曹天钦先生的研究生;还有从生物实验中心合并到生物物理所的郭尧君等。我们几个年青人一起愉快地工作,做了几篇研究论文。除了李书记,我还要感谢业务处韩兆桂处长、感谢所领导把我调到了一个有事情可以做的地方。
实验中发生过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一天中午,我到在北大工作的姐姐家去了,等我回到实验室看到的景象让我顿时倒抽一口冷气。一个做蛋白质冷冻干燥抽真空的干燥器爆炸了,二十多平米的房间遍地是玻璃碎片,我有一件挂在水池子上的游泳衣已被磷酸腐蚀成了碎片。在斜对面实验室工作的邹承鲁先生看到我回来了,对我说,他听见爆炸声后马上过来,但门锁着,就只好从门上面的窗子爬进去查看发生了什么。邹先生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还要从2米高的门上面的窗子爬进去,多不容易啊。通常我中午都是在实验室吃饭和做实验的,如果那天也是这样的话,那么厚的玻璃干燥器就在我身旁爆炸,最好的情况我也肯定是一个“宋丹萍”了。后来,我们在抽真空的干燥器外加了一个铁丝网罩子。我从德国回国时就向洪堡基金会申请买了一台冷冻干燥仪回来。
“文革”后期,我们科学院高瞻远瞩,在国内最早办了英语口语班,请中科大的李佩先生组织教学。我跟王书荣在一批,好像是第二届(1975-1976)。我不是党员,不是干部,也不是工农干出身,但是七室领导让我去学习,我特别感激实验室的支部书记徐秀璋。
在科大(合肥)学习的一年从根本上提高了我们的英语水平。紧接着改革开放,外宾越来越多。外事处的负责人亢宏老师常会把我叫去做“翻译”。我30多岁才张嘴学口语,而且就学了那一年,真是赶鸭子上架。我记得有一张照片,王大成在给来访的日本科学家讲胰岛素晶体结构,我在旁边给他当“翻译官”。
后来,科学院在国内首次与德国洪堡基金会达成协议,选派访问学者。所里又推荐了我通过洪堡项目到德国羊毛所工作。羊毛所正是世界上三家成功合成胰岛素的实验室之一。
我从德国回来时已经40岁了,主要是做生化研究;而梁栋材先生的研究室完全是做晶体结构,我没有意愿再从头去学晶体结构解析,于是希望调到做生化的研究组。最后我被调到邹承鲁先生组。我的科研工作最早的源泉就是来自我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胰岛素合成中的蛋白质折叠问题,也就是胰岛素的两条肽链为什么能够在溶液中自发生成活性胰岛素分子?这正是邹承鲁先生在上海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后到北京开展的一个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我参加了这样一个被戏称为“老题新做”的胰岛素A、B链重组的基础研究,希望探明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的原因,揭示其中的蛋白质折叠问题。我作为邹先生的co-PI获得了美国NIH十几万美金的研究基金。NIH向国外发放研究基金一般只支持在美国国内无法进行的实验。我们的胰岛素A、B链重组的基础研究并不属于“在美国国内无法进行的实验”,所以获取到这份研究基金十分不容易。80年代初十几万美金相当于一百多万人民币,对我们从国外购买仪器和试剂非常有帮助。我开始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来催化和促进A、B链重组成活性胰岛素的研究。我运气不错,为以后开拓折叠酶和分子伴侣的新领域奠定了基础。

1977年,英国科学家D. Hodgkin来访,与胰岛素晶体结构研究组人员合影
后排左起:饶子和,张明安,王家槐,张思和,董贻诚,梁栋材,吴伸,G. Dodson,常文瑞,D. Hodgkin,郑启泰,唐有祺(北大),雷克健,戴金壁,钟纳天,林政炯,李家遥,王大成,毕汝昌,伍伯牧
前排左起:楼美珍,王玉英,顾孝诚(北大),窦士奇,宋时英,王志珍,桂露露,沈福苓,张树德,王耀萍,梁丽,林秀云
分子生物学是上世纪70年代兴起和发展的。而70年代正是我们的“文革”时期,当时国内和所内真正做分子生物学的人很少。我意识到,做生化研究如果不懂分子生物学是没有出路的,所以80年代中期我又去美国学分子生物学。回国后建立了分子生物学的技术体系,重点实验室其他组的学生也到我们组来做蛋白的克隆、表达、纯化、鉴定等。现在的年青人恐怕很难想象30年以前的情况。
回想起来,我真是非常感谢生物物理所领导以及二室、七室、十二室的领导,他们在我人生转折点中给了我很大的理解、包容和帮助。我愿意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激之情。现在“跳槽”是太平常的事了,可是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

2007年中国科学院结构生物学战略研讨会上部分科学家合影。左起:常文瑞、施蕴渝、王志珍、梁栋材、王家槐、王大成、汪必成
我在邹承鲁先生实验室开始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研究。邹先生是酶学泰斗,他喜欢用自己提取和纯化的酶来做实验,这样更掌握酶的脾气。所以我们一清早到大红门屠宰场去买牛肝,从新鲜牛肝中提取、纯化、鉴定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来做实验。我在加拿大工作的时候,注意到1987年才发现的分子伴侣新概念。由于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来催化A、B链重组成活性胰岛素的研究经验,我根据对分子伴侣新概念的认识,回国后的当年与邹先生共同在《自然科学进展¾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讯》发表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多功能”的文章,提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是否还可能在新生肽链折叠中起着更为普遍的分子伴侣的作用?”;我被推荐在第七届全国生化大会上做了有关内容的大会报告;最后与邹先生共同在《FASEB J》提出“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 is both an enzyme and a chaperone”的假说。此后便开始了在这个新领域里的不断耕耘,为我们提出的假说提供翔实的实验证据。现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是分子伴侣”已被国际同行普遍接受,国际上和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对其结构、特别是生理功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国内外一些实验室主动来与我们讨论和合作有关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研究。邹先生治学的创新思维和严谨态度影响了我一生的科研活动。

2000年,蛋白质功能与酶学研究室人员合影,前排左起:田玉兰、王志珍、静国忠、王志新、邹承鲁、刘江红、周筠梅、王金凤
我还要感谢国家重点实验室梁栋材、杨福愉二位前辈科学家对我的教导和栽培。梁栋材先生推荐我在第四届全国生化大会上做了“胰岛素分子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复杂性”的大会报告,整理后联名发表在《生物化学杂志》。后来听说原来是梁先生自己被邀请做大会报告的,但他坚持推荐了我这个小人物。后来我又在梁先生的指导下,在《生理科学进展》共同发表了“当今胰岛素研究的趋势——胰岛素作用机制的阐明”。1977年,梁先生的恩师、诺奖获得者Dorothy Hodgkin第四次访华,梁先生指派我陪同Dorothy和他的学生Guy Dodson在北京的访问。1993年,我又幸运地被梁先生指派撰写“Dorothy and insulin crystallographic research in China”的文章,这是梁先生应印度物理学家Ramaseshan邀请为Dorothy出版的四部论文集写的,为此梁先生给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指导我如何写这篇文章。此文还发表在《Current Science》上,后应《化学通报》要求翻译成中文。杨福愉先生推荐我在第六届全国生物膜学术讨论会上做大会报告,后来又推荐我在亚洲大洋洲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合会(FAOBMB)任中国代表,使我在国际学术组织和活动中受到新的历炼。

2006年,在杨福愉先生80岁寿辰时杨福愉(左)与王志珍(右)合影
我觉得所有在科学院里成长的人都受益于科学院的好领导。科学院的领导既讲政策又注重人性化。科学院没有多少“右派”,听说这是因为张劲夫院长冒着巨大的危险保护了一大批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否则“两弹一星”从哪儿来?科大也是科学院老一辈科学家亲自办起来的,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在前沿、交叉领域理工结合的人才。直到现在,科大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仍然牢牢地站在前列。
访:今年是建所60周年,请您谈谈您的感想。
王:我有一个看法,不见得对。“文革”之前,生物物理所在国内的地位没有上海生化所高。他们有中国最好的一批生化学家,做了很多知名的工作。国际上了解得比较多的是上海生化所。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化所走失了一批人才,很多人出了国没有回来。而在同一时期,邹先生和梁先生调到了生物物理所,对生物物理所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邹先生建立的酶学开放研究实验室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开放实验室;在此基础上,邹承鲁、梁栋材、杨福愉三位先生建立了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我们所出国的一批人基本都回来了,如王志新、王大成、常文瑞、陈润生、王书荣、郭爱克,毕汝昌、周筠梅、沈恂、沈钧贤等等,形成了生物物理所的中坚和骨干力量,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神经生物学舞台上的主角。

1996年5月邹承鲁先生(中)与王志新(右)、王志珍(左)合影
酶学和蛋白质研究方面,邹先生带领的酶学团队获得了六个国家自然科学奖。晶体结构方面,物理所做胰岛素晶体结构的一批同志合并到生物物理所,在梁先生的带领下形成了中国蛋白质晶体学的摇篮。在此,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人——林政炯。他是王家槐、王大成的老师,是生物物理所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的杰出代表,非常优秀,但为人十分低调,是一位与世无争的人,我们都尊重他。杨先生留苏回国后到生物物理所工作,他的团队无疑是国内生物膜研究的主要高地。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立是生物物理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里也是中国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实验室。通过这个实验室,人才被凝聚起来,力量就爆发出来。创立至今的三十年中,每次评估都是“优”!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生物物理所一枝独秀,在国内的生物学领域占据独一无二的辉煌地位,并在国际舞台占领一席之地。进入新世纪,随着政策的改变和国家的发展,特别是高校的崛起,在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版图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的高峰,生物物理所还是屹立在高原,而且在国际同行中赢得越来越高的声誉。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进入新的时代。我们生物物理所要永远创造新的高峰,高峰要高到无穷!
访:请您对年轻人说几句话吧。
王:近年来,大批新的、年轻的优秀人才加盟我们生物物理所,他们比我们做得更好,他们以及更年轻的科学家是我们研究所的希望和未来。
邹先生曾跟我们讲,他们当年就只有一台分光光度计,做的实验现在看来都是古老教科书上的那些实验。但是就是在这样落后的条件下他们能做出那么多成果,多不容易!“文革”后期,邹先生在剑桥时的同学、E. Smith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访华的美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到邹先生实验室参观。那时邹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工作全部停止,为了应付,实验室试剂瓶里面都装上了自来水。过了若干年以后,Smith对他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什么也没干”。“文革”使我们失去不止十年,危害不止一代人啊。
现在的这代人比我们那一代人强,土壤就不一样嘛。我从三十五、六岁才真正开始做科研工作,现在的学生从大学二、三年级就进了实验室。现在我每次路过和平门南边那条路,都会想起以前向国外投文章要自己画图,还必须倒两次车到和平门的新华社去制图,常常要跑两三次才能把图做好。
每个人的命运都跟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是战争年代,你就得去打仗。抗战时,邹先生在西南联大就参军当了汽车兵,在滇缅公路上运送军事物资。多少人从悬崖上掉下去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要感谢你们所处的这么好的时代,要珍惜现在这么好的科研环境,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好科研环境。希望年轻的科学家们要对得起这个伟大的时代,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资料
[1] 微信公众号“中国生物物理学会”(ID:BSC-1979),王志珍院士访谈录|生物物理所赋予我科学的生命
声明:化学加刊发或者转载此文只是出于传递、分享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认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电话:18676881059,邮箱:gongjian@huaxuejia.cn